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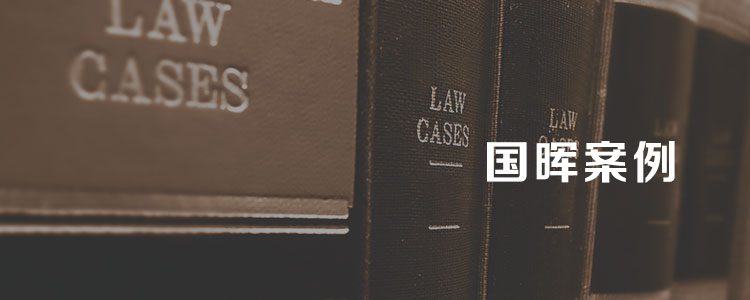
 404
404本文是陈亮婷律师在2014年,代理某新加坡外商起诉中国国内某公司及股东,成功索偿股权转让款及分红约¥500万元的成功案例。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有关当事人为化名。转载请注明出处:深圳陈亮婷律师成功案例集http://www.cntoplawyer.com。如需法律咨询,欢迎致电13828882493
案情简介:
新加坡外商以¥500万元购买了深圳市RB科技有限公司(下称RB公司)30%的股权,登记在RB公司股东之一刘M的母亲伍某名下。投资半年后,新加坡外商与公司两个股东张B、刘M发生矛盾,退出了RB公司,便与张B、刘M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张B、刘M以¥400万元共同受让新加坡外商的24%股份,分别在2012年6月30日、2013年6月30日前各支付¥2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而剩余6%股份仍由伍某代新加坡外商持有。三人一并在该协议上作出了分红决议:RB公司应在2012年12月30日前支付新加坡外商转让股权之前的分红52.5万元。但张B、刘M夫妇并无按约定支付股权款给新加坡外商,RB公司也无支付分红给新加坡外商。
因此,新加坡外商委托陈亮婷律师,根据该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前后两次向深圳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分别要求张B、刘M支付前述两期的股权转让款,要求RB公司支付分红款。
裁判亮点:
该案涉及外商隐名投资的股东身份确认和股权确权等疑难点,更涉及到法院的司法权和外商投资主管部门的行政审批权“打架”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此问题虽有原则性指引规定,但立法上仍存在操作盲点,对于涉案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这一关键问题,两次仲裁庭的仲裁席在无明确法律规定的情况下,采纳了陈亮婷律师的代理意见,引用法理断案,认为:隐名的新加坡外商的投资虽未经外商投资主管部门审批这一法定程序,但其投资的目标公司的经营范围不属于外商投资限制或禁止的产业范围的情况,隐名外商转让公司股权的行为合法有效。特别是第二次仲裁中,首席仲裁员深圳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千华教授对此问题,从法理上作了透切的阐述。
以下截选了部分精彩的仲裁理由:
………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生效之后,关于合同效力判断问题,一个基本的社会共识是:应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认同合同的效力,除非合同违反效力性强行法律和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未取消或减损上述社会共识,其制订目的是在尊重行政审批权的前提下,尽可能保护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的主要内容是:申请人有义务指令伍某将其持有之第三被申请人相应股权转让给第一被申请人和第二被申请人;第一被申请人和第二被申请人则有义务向申请人支付所谓“股权转让款”;第三被申请人有义务向申请人支付所谓“分红款”。按照该约定,股权变动登记的前后,第三被申请人的登记股东均为中国内地自然人。上述约定均在主观上无意图,在客观上亦未导致第三被申请人的企业性质的变更。因此,该协议书本身不属于设立、变更外商投资企业的相关合同,无需审批,合法有效。
其次,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将物权效力和合同效力予以区分,本案所涉股权的效力和涉及股权投资的合同效力是两个应区分的概念。尽管《股权转让协议书》使用了“股权转让”、“分红”等企业组织法上的用语,但其性质是一个关于申请人作为实际投资人退出投资而非入股的债权债务约定,其本意并非为申请人设定法律意义上的股权,而是使申请人获得债权。换句话说,即便在申请人和第一被申请人、第二被申请人之间曾经存在的、未经行政审批的、事实上的“股东合同关系”可能具有效力上的问题,但作为意在终结该“股东合同关系”的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目的则只是为申请人在终结上述“股东合同关系”后获得债权。“股东合同关系”的效力缺陷不应影响意在终结“股东合同关系"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因此,申请人尽管未获得法律意义上的股权,但不影响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合同效力。
最后,申请人未获得对第三被申请人法律意义上的股权,只是意味着申请人不能行使外商投资企业法或公司法企业组织法所赋予的股东权,但这并不当然意味着其不得主张依据合同法使其作为隐名股东和实际出资人的隐名投、地位以及由此产生的投资权利和义务取得保护。企业组织法和合同法是并行且具有同等地位的法律,不能以某一个法律为依据否定当事人从另一个法律获得的权利保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申请人的权利名为“股权出让所得”和“分红”,其实质是申请人投资产生债权的获得。

请使用微信"扫一扫"做您的掌上律师

国晖小程序